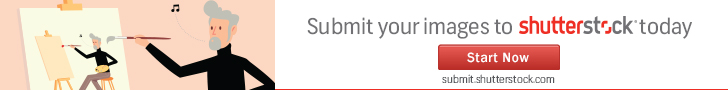|
| 阿曦和他别借走的十年光阴。 |
"发病十年才来就医是在搞什么呀?" 同事拉拉与我在前往紧急部门的路上无奈的说道。
“家人容忍度极高。或许是这样的。”我略略回答。
十年,到底长不长?
阿曦今年二十八。
发病五年前,曾经到大城市去就医,因无法配合药物治疗,病情每况愈下。十年前,阿曦十八——那个挥霍繁华青春的时光;那个一跃既是美好未来的岁月。阿曦和其他的孩子一样,认真念书,和其他孩子一样,当时也盼望未来似锦前程。然而,十八岁之后的日子,并非想象中的一帆风顺。
紧急部门那天有些吵杂。阿曦的手脚被绑在担架上。他躺在担架上,手脚努力的尝试挣脱宝石绿色布条的捆绑。
阿曦高高瘦瘦的,凌乱的长发盖住了他的额头。他不时甩甩头,试图把油腻的长发甩开。阿曦双颊凹陷,夹着一副眼镜, 那是一副花得可以的半框眼镜, 小小的一副。那那看起来是十几年前潮流尖端的眼镜吧。
“阿曦,今天跟谁来医院呀?”我温柔的问阿曦。
“跟哥哥,跟警察叔叔。” 阿曦用浑浑噩噩的口吻回答。
“阿曦今天怎么了?”我问带来就医的哥哥。
“他用木棍打了老爸... ... ”阿曦的哥哥大略跟我叙述在家发生的事情。
"他早前是个很乖的孩子,在家排行老幺,曾经我们都以为他会有一个很美好的将来。发病之前,他是个很勤劳温和的孩子 。十八岁之后,也不知道怎么搞的,好像变得懒散。之前念书都是数一数二的。后来快毕业的时候,成绩越来越差劲。虽然毕业的成绩单满江红,他还有到城里去找合适的科系想继续念书。后来好像课业跟不上,只好飞回来继续住在家里。那些日子,虽然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,他还是有很努力找工作,帮忙管理燕屋之类的... ...后来的日子就越来越可怕了,他的房间里藏满了利器,成天喊打喊杀。我真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... ... "哥哥侃侃而谈,叙述他所认识的弟弟和后来的弟弟发生的所有事。
“藏利器在房里为了干嘛?你们知道吗?” 我继续问。
他说要防身用。第一次我们带去就医的时候,我也忘了是什么事。我想大概是觉得他变得奇怪。医生开药之后,我们带他回家,劝他好好吃药。可怕的事情后来就发生了。他开始对家人起疑心,觉得我们全家都想要毒害他。也因此,他不吃家里平日妈妈煮的料理。虽然说他情况好像蛮糟糕的, 但是每天还可以自己给自己煮饭, 说起来也蛮奇怪的。他不准我们碰他的食物,说我们都想要预谋毒死他。那样的情况,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医生开的药给他好好服,病情变差,带去复诊变得更不可能。”
“所以后来又过了五年没有治疗的日子吗?” 我继续问。
“是的。锅子烧坏好几个,但这些都还好。我们有发现,他近年来越来越没有办法照顾卫生,乱七八糟的房间,发出恶臭的卫生间......” 哥哥继续说。
后来阿曦住院,由哥哥陪同。那个晚上,在抵达病房的时候,我把捆绑他的布条解开。护理师细心地解说一遍住院流程给阿曦和哥哥。
由于阿曦的幻觉一直围绕在家人想要用食物毒害他,住院的他不吃不喝,也不肯吃药。也因此,我们照三餐给他打了针,让他好好休息。阿曦起先在病房里并没有闹事,只是静静的睡。
第三日一早,阿曦因药物产生徑症狀。说时迟,那时快,阿曦歪头,牙关紧闭,持续痉挛的肌肉让他感到疼痛,疼痛得无法言语。
“我要普环啶!准备!十五号床徑症狀!” 我向正在发药的护士求助。
一剂... ... 再一剂... ... 总算好些了。
那一天,阿曦睡了一个下午。
凌晨两点,护士打来,让我过去看看他。
“赶快来,病人他要越床而下, 他说他要去买菜。我们就要管不住了。”电话那头传来护士焦急的说话声。
睡眼惺忪的我,撑起伞,在雷电交加的午夜,穿过藤球场,再走过草场,飞奔到病房。那晚风很大,我的鞋子在奔跑中被草地上的积水弄湿,狂风暴雨也把我的黑色裤子弄得湿透。
“让我出去!我要去买菜!大家都在笑我不可以煮东西!我要起来煮东西!你看他们在煮东西!”阿曦指着远处墙角一直在咆哮。那夜,阿曦的幻觉,把整个病房搞得鸡犬不宁。
湿哒哒的我,站在病床旁试图安抚阿曦。这个脚趾头泡在湿透的鞋袜里,真让人不舒服。
那个晚上,我给阿曦打了好几剂药,他才缓缓睡去。
阿曦一连住院七天,后来幻觉渐渐在服药之后慢慢减缓。他和哥哥开始在病房里有说有笑。哥哥频频走到柜台来跟医生护士道谢,他觉得弟弟如今能够回到生病前的样子,好不可思议。
这天早上阿曦起得早,八点钟准时坐在床上等医生来巡房。
“阿曦,早!”我和阿曦打招呼。
“早,早啊。” 阿曦有点腼腆。
“我想知道我生什么病,我想我好多了。那天这个左手有打针是什么样呢?我记得右手也有打两个,不知道是干嘛的... ... ”这问得真有点意思。
“如果医生你检查了我好多了,那我想回家了。” 阿曦继续问。
“那么快 想回家了吗?哈哈!阿曦,想回家干嘛?”我调侃他。
“我... ... 我想要去找工作了。” 他说。
“找到工作了哦?”我边翻病例边问。
“找看看... ... 再找看看... ... 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做的。”阿曦继续说。
“阿曦今年几岁?”我问。
“我... ... 我... ... 十八,吗?”他困惑。
后来家人把他的房间整理好,期待他回家。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,我们准许他出院。出院前,我和阿曦坐在病床边,我重复教导他的病状,不断提醒他药记得吃药。
“思———觉——失——调——”我说。
“丝——市——丝——解——觉——丝——调”阿曦跟着念了好几次。
阿曦的出院,让我有些感慨。他有很好的家人,在住院期间轮流来陪伴他。在这个内科病房照料精神科病患,真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。(就像借住他人家还不断给人家添麻烦的概念)
我想这是我从没想到过的新挑战。早前在病房服务的日子,有精密训练的专科护士,有尽责的职能治疗师... ... 如今,只能够亲力亲为。
我再次打开课本,细读这段前些日子读的段落:
 |
| @SPMM |
呀!十年。
那是阿曦人生岁月里,他和他被借走的十年。
阿曦的十年,经历了什么?
我们,又经历了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