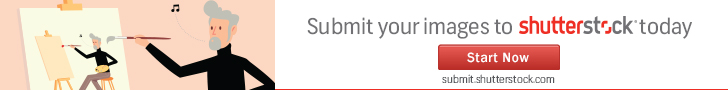周三的诊所,病人很多,来来往往的。我在医院为病人跑腿办点文件,最后终于坐下来好好看诊。
他扶着太太,坐上诊疗台。
三年前中风后,双脚在数个月的复建后恢复行走能力,但有些缓慢。
“来,双手举起来哦,医生帮你检查一下。” 我说,边温柔的把她双手固定在头上。
她左手牵着中风后瘫痪的右手,不好意思的跟我说:“不好意思医生,我的右手有点不方便,有些笨拙。”
“没关系,我们慢慢来。”我说,边做触诊。
“好了,可以起来了哦,慢慢来没关系。”我打开帘子,先生走进帘子,把太太扶下床,稳稳的坐回轮椅。
“看起来好像是脂肪瘤哦,我们做个超音波,然后再做一个細針抽吸細胞診斷。这里要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个細針抽吸細胞診斷的步骤和风险。首先是……”我开始解释病情和诊断流程。
“好。”她坐在轮椅上,点点头,微微笑的。站在身后点先生也静静的听。
“如果赞同,可以在这里盖个章。请问有什么疑问吗?”我把同意书递过去。
“没有。” 太太说,摇摇头,笑容依然温柔。
她抬头看了看先生,先生也点点头,看着太太好温柔的点了点头。
“先生,有什么疑问吗?”
我问。
“医生,不好意思,我都明白,只是…
… 还是想问一下,这个細針抽吸細胞診斷会危险吗?” 先生问。
“对于初步诊断,相较于切除活检,細針抽吸細胞診斷相对… … ”我再解释一次。
“好。好… … ”
他点点头,若有所思。
“先生,很担心吧,还有什么疑问吗?没有做过細針抽吸細胞診斷,会担心是正常的。流程都理解吧… …“ 见先生有些担心,我多说了两句安抚他。
“没事医生,我只是想多问一次。我担心我的太太,太太只有一个… … “双手轻轻拍了太太的肩膀,看起来有些心疼内人。太太抬头看着身后的先生,笑得暖暖的。
我们在理想化的世界里,我们都忘了爱可以多么伟大——亲爱的,爱是包容、爱是接受… …
我们的不完美,让彼此都真實且完整 ...
你若不离不弃,我必生死相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