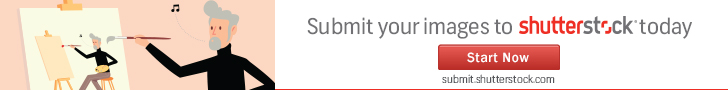“嘿,身体还好吗?今天也先生陪你过来吗?”我走进化疗间,在洗手台洗手,边慰问。
“嗯。”她戴着鼻导管,安静的躺在化疗间的病床上。
那天是二零一八年的十月三十号,专科医院调派来的肿瘤专科到访,我们在化疗间忙进忙出。
“你认识我文章里的女主角吗?——我爱你深深的 那篇文章的女主角。” 我边忙写病例边问同事杰棋。
“她今天也有过来吗?”他睁大眼睛问了问。
“对啊,化疗间左手边角落那张病床上,只是上次看到她的时候还没戴鼻导管。” 我说。
“哦,真的哦。”他探头看。
“恐怕很快,我们就会在病房遇见她了... ...”我迅速整理凌乱的病例,捧着沉甸甸的文件离开。
再来遇见,是十一月十号。女病房——病床十三号。
她还清醒,只是戴着的也不是鼻导管, 她已需要高流量氧气——近乎一个放棄復甦病人能够拥有的最后专利。
再来就是三天后,我结束上午的手术,午休后回病房巡房。
“十三号呢?”我问同事李娜。
“转出去了。”她神情淡定的回应。
“去哪儿?放棄復甦的病患不可能去加护病房吧。还是情况那么好转离这个危急的隔间...”我疑惑。
“转到了天堂。” 李娜打断我的话。
“好吧,还是离开了...” 我回答,心情郁郁的,但也没多说什么。如此平静。
隔天在化疗间,我问我最喜欢的化疗护士小杜说:“你为什么要当化疗护士,不总是很郁闷吗?”
“误打误撞的,后来也做了十几年。”她边整理文件边说。
“怎么突然这么问?”她接着问。
“病患林阿娴左午过世了。” 我说。
“嗯。死因是什么?” 她低声的问,语气有些讶异,又有些习以为常,有些矛盾的情感。
“我不清楚,昨午我没多问,同事只说法医部门的担架刚离开。” 我回应。
“嗯。”她没说什么,继续专注的点算化疗的药物。
“我怎么觉得患癌后期的姑息治疗好让我忧郁呢。”我说。
“怎么了。” 她问。
“那么用心照顾病患,最后的结果都一样... ... ” 我感慨,似乎有些吃不消。
“对啊,有时候看单子上,某病患突然不来化疗了,我们都会打电话到家里去慰问。这些时候得到的回应,蛮常都是从家属口中得知某病患早已离开。”她温柔的说。
她转过身来,拍拍我的肩膀,知道我难过。
“你都不难过吗?”我问。
“会呀,但病患和我们,不都已尽力了吗?” 她回答,而我突然泫然欲泣...
纵使在服务患癌病患的这阵子,常让我消极又沮丧... ...
这天早晨,我和同事吃过早餐后,到诊所值班,看了这天的第一个复诊病患
“早呀!哉蹾女士,今天的第一号病患呢!在家的生活都还好吗?”我问。
她坐下来,微微笑的,看起来精神颇好。
“好啊,都很好。胃口不错,状态也蛮好的。生活都很好... ...”她侃侃而谈。
“好棒哦!近期都在做什么呢?”我边写病例边问。
“我都还在工作呢!我跟你说哦,我从事餐饮业,在帮别人包伙食,小的可能是个人左右,大的可能是婚礼的伙食,旗下十几个工人,一起包办伙食,大家好糊口......"她侃侃而谈。
她是个肺癌,做过肺叶切除手术的病患,术后恢复的很好,如今还开始忙起了小生意。
“好呀!下次部门的小餐会,我给你打电话哦!”我说,好快乐的。
“岚医生,结婚典礼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吼... ...” 护士姐姐调侃我。
护士还参考起了菜单... ...
诊间里,快乐的气氛氤氲。